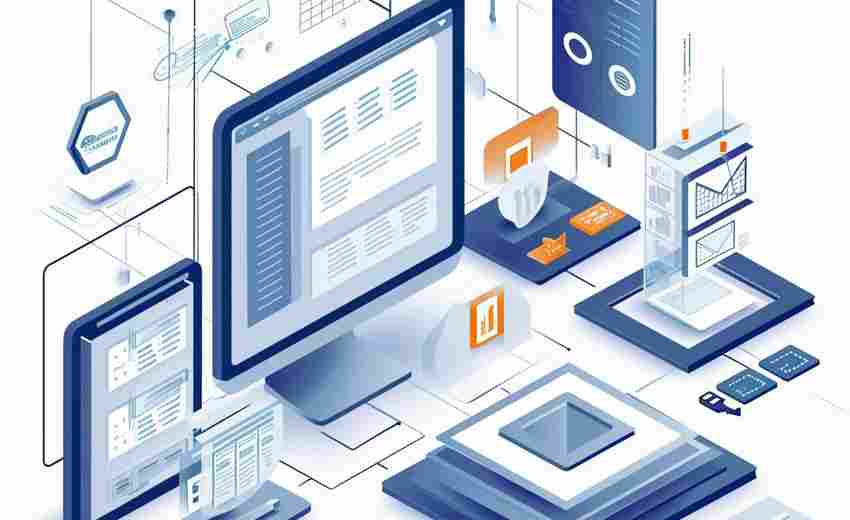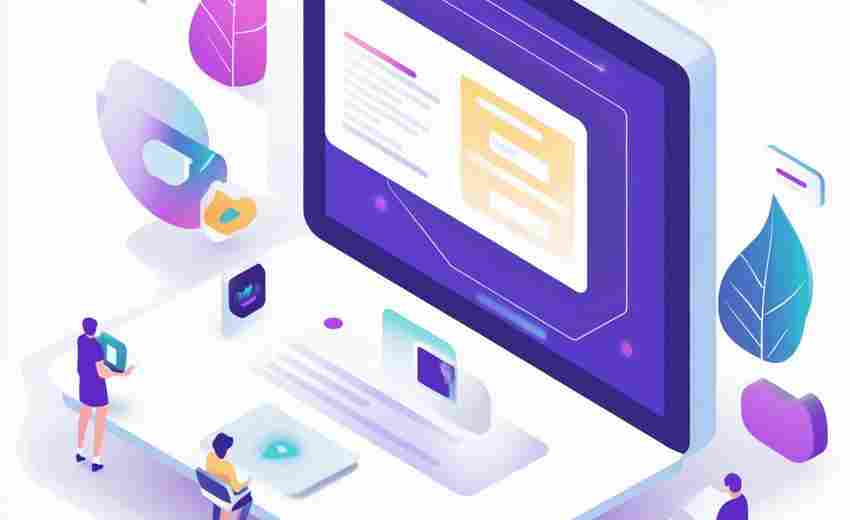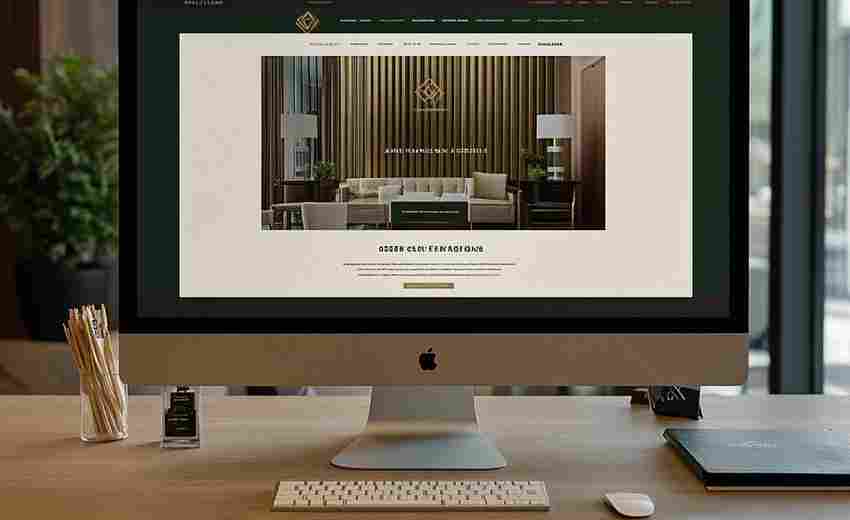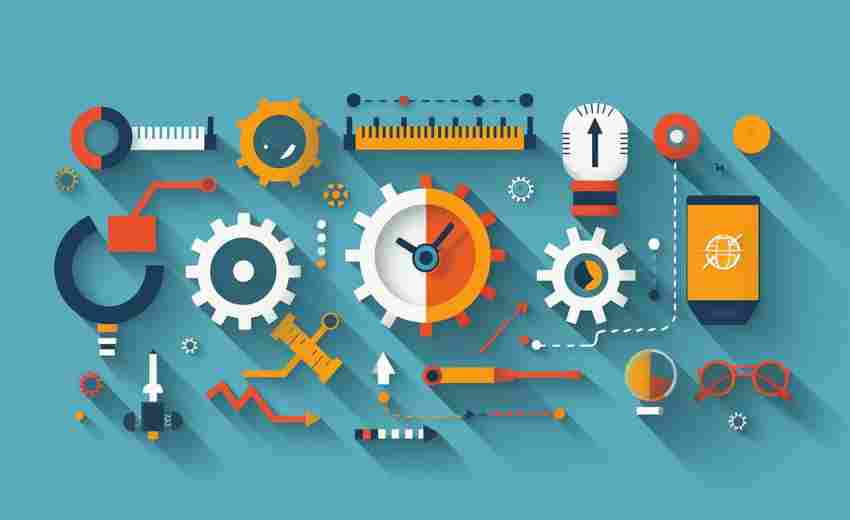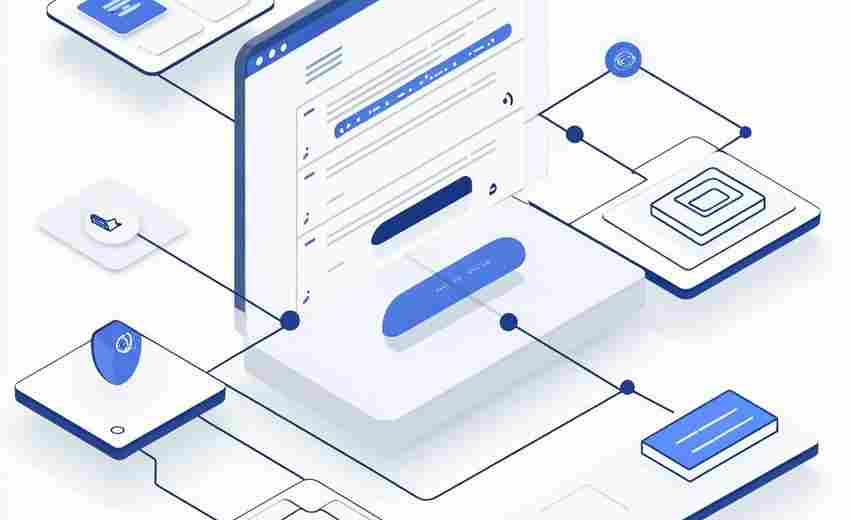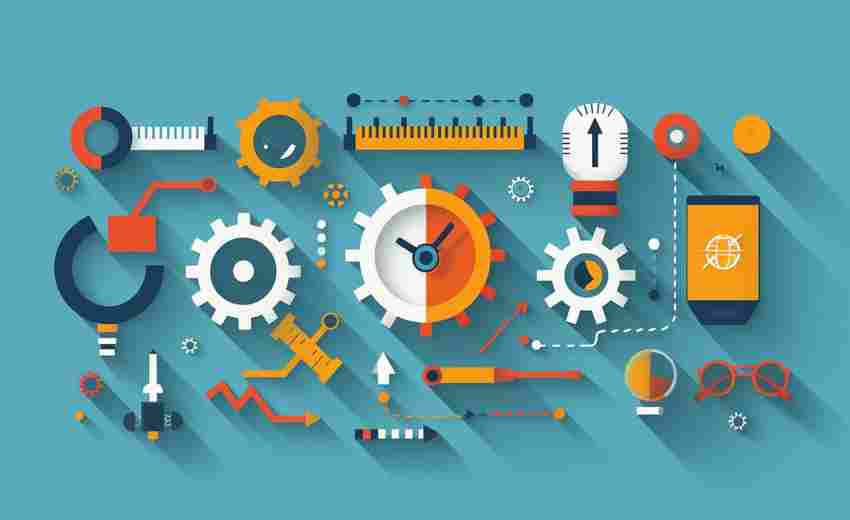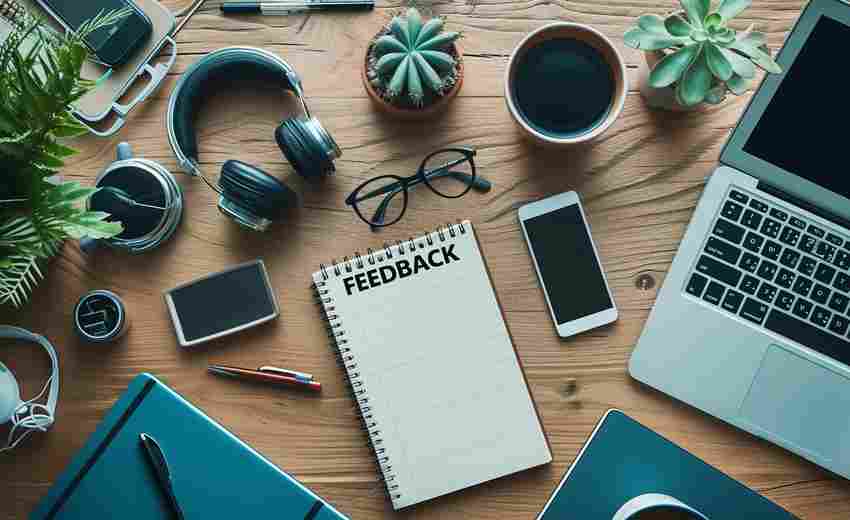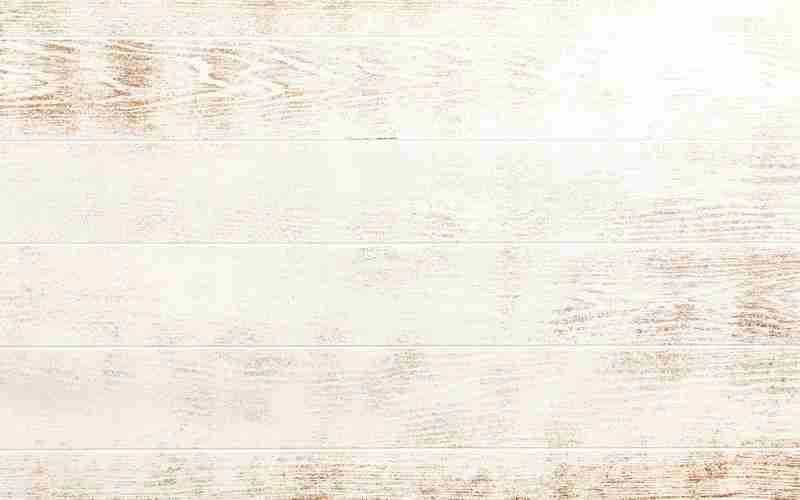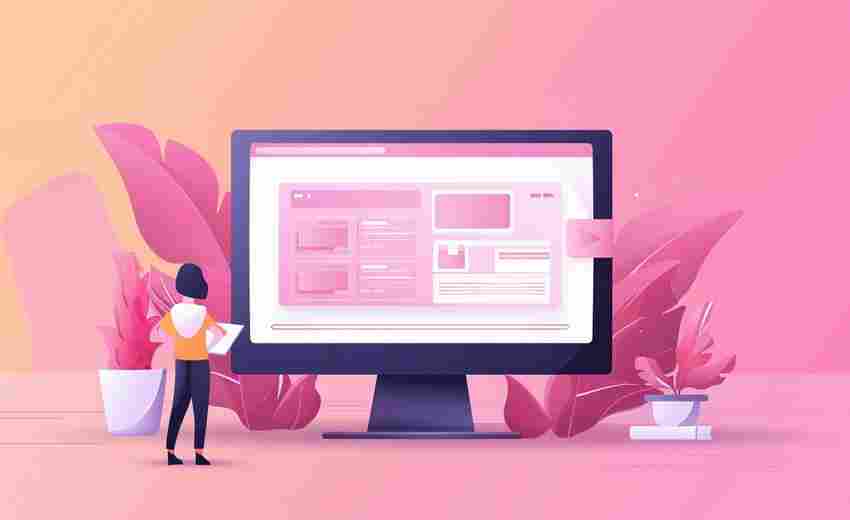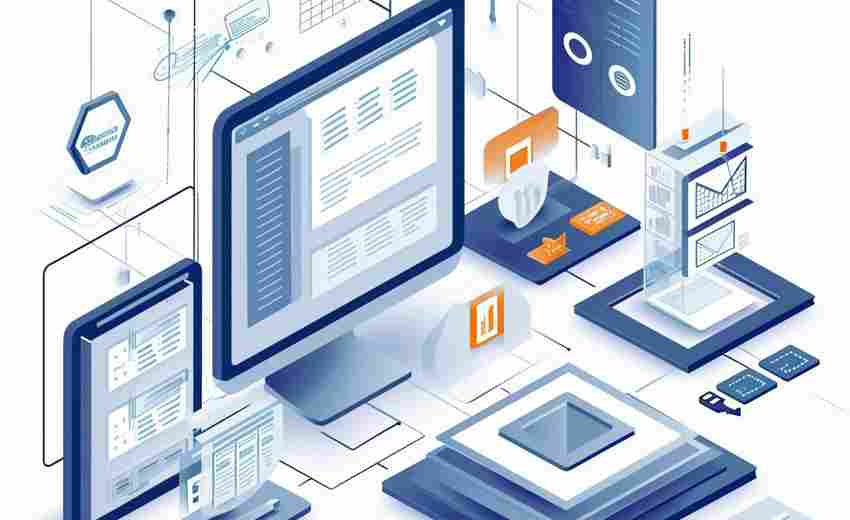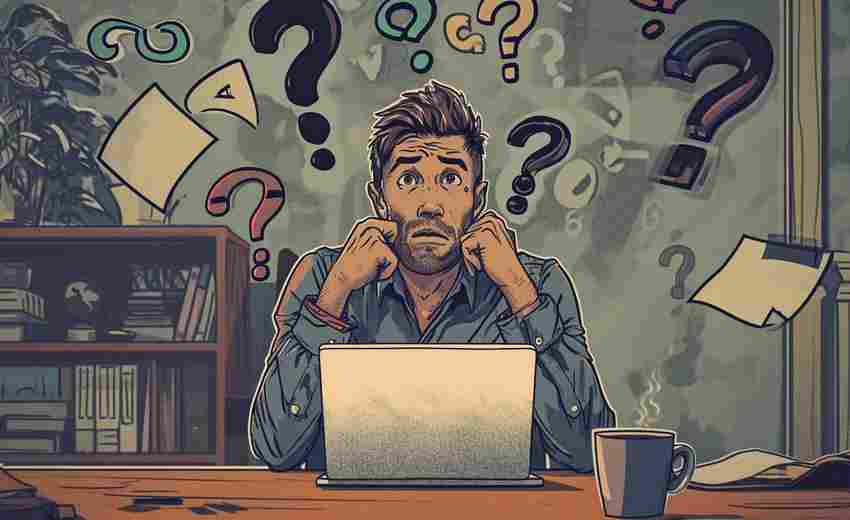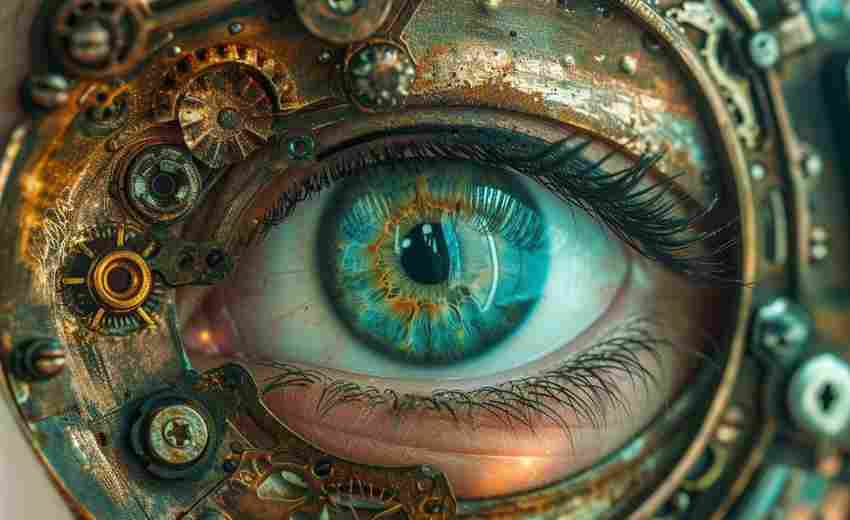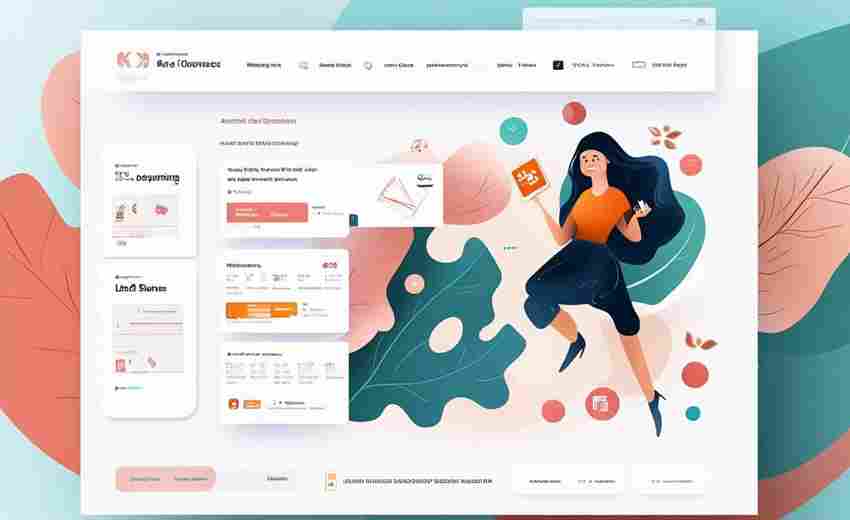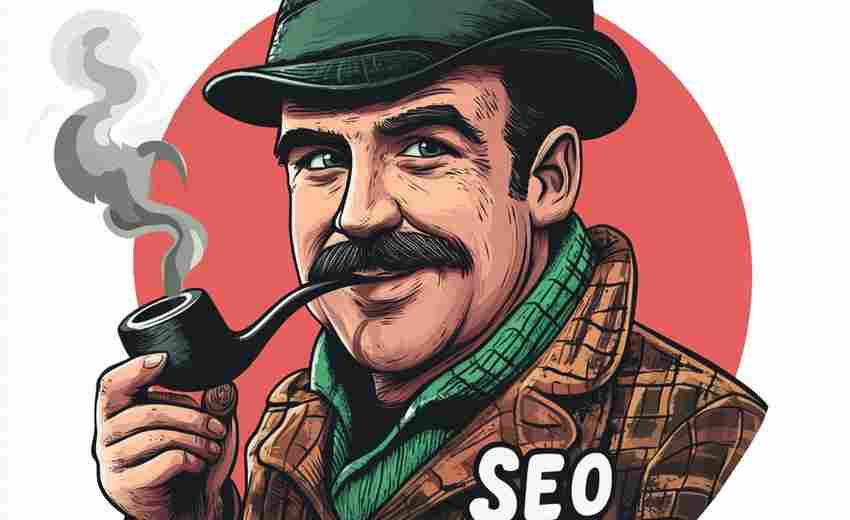在算法主导的流量分配体系下,搜索引擎与社交平台间的数据关联性日益增强。部分从业者利用这一特性,将社交媒体刷量作为SEO优化的灰色跳板:通过伪造互动数据、操控算法指标,制造虚假流量并反哺网站权重。这种游走于技术与规则边缘的“双向作弊”,不仅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,更催化出新型网络黑产形态。
技术实现路径
社交媒体刷量的核心技术可分为硬件模拟与软件攻击两类。硬件层面,“群控系统”通过USB集线器同步操控数十至数百部手机,利用脚本程序模拟真人点赞、评论、转发等行为。入门级群控设备可控制30部手机,报价约3万元,其规模化操作能使单日虚假互动量突破10万次。软件层面,黑客常采用“暗链劫持”技术,将境外、网站代码嵌入正规平台后台,诱导用户点击跳转。2020年北京警方破获的案例显示,犯罪团伙通过暗链日均引流超50万人次,非法获利逾千万元。
技术迭代使作弊手段更具隐蔽性。部分灰帽SEO从业者结合AI生成内容与分布式IP池,创建“半自动化刷量系统”:由AI生成个性化评论内容,通过动态IP切换规避平台监测。某案例中,某营销公司使用该技术将客户网站在Google的搜索排名提升至前3位,日均获取自然流量增长300%。
风险与法律边界
数据造假的法律风险呈跨国界、跨平台特征。我国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明确将流量造假纳入违法范畴,但刑事立案标准尚未统一。2021年广东某刷量团伙因虚构App下载量骗取推广费被起诉,法院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,涉案金额认定成为量刑关键。民事领域,某电商平台因炒信被判赔偿竞争对手200万元,开创流量作弊民事追责先例。
技术滥用衍生出次生危害。虚假流量常被用于传播虚假信息,如2020年境外势力利用2903个推特账号集群式散播新冠病毒谣言,相关话题单日转发量超百万次。清华大学沈阳教授指出,流量造假与算法推荐的结合可能形成“信息茧房效应”,使极端观点获得不成比例的传播权重。
行业生态影响
灰产链条已形成完整利益共同体。上游提供技术工具开发,中游运营刷量工作室,下游对接企业主与个人用户。某暗网交易数据显示,社交媒体万粉账号售价约500元,十万级互动量套餐标价8000元,形成“需求驱动供给”的市场闭环。这种畸形生态挤压了合规企业的生存空间,某第三方测评显示,旅游类网站的自然搜索流量中约23%被刷量网站劫持。
平台治理陷入“猫鼠游戏”困境。抖音2020年封禁6.7万个违规直播账号,但新注册作弊账号平均存活周期仅72小时。部分平台为维持估值增长,默许一定程度的流量泡沫存在。北京理工大学闫怀志教授将其比喻为“皇帝的新衣”——平台与刷量团伙形成心照不宣的共生关系。
应对策略与治理
技术反制需建立跨平台数据图谱。腾讯防水墙团队开发的多维行为识别模型,通过分析设备指纹、操作频率、行为轨迹等238个特征参数,可将虚假账号识别准确率提升至92%。欧盟推行的《数字服务法案》要求平台公开算法核心参数,为外部审计提供可能。
治理体系需突破单点监管模式。建议建立“三位一体”防控机制:司法层面明确流量造假刑事立案标准;监管层面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;行业层面推行第三方流量审计制度。某省级网信办试点项目显示,引入区块链技术进行流量存证后,区域内网络诈骗案件下降37%。